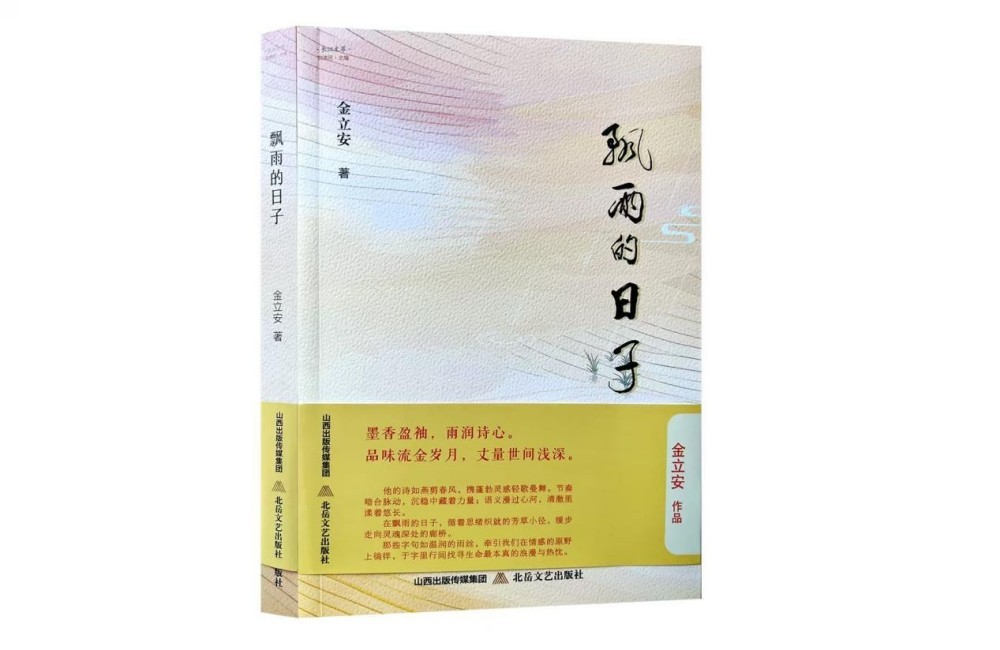
在当代诗坛,金立安先生是一个独特的存在。他既曾手持法槌,于庄严的法庭上裁断是非;亦曾执掌文牍,在文化的疆域里擘画蓝图。如今,在花甲之年捧出的诗集《飘雨的日子》,并非一次职业生涯的余韵点缀,而是一部以生命为纸、阅历为墨完成的“跨界书写”的深沉证言。这部诗集的艺术价值,恰恰在于其内部始终进行着的一场静默而激烈的对话——法官的理性凝视与诗人的感性澎湃之间,公共身份的社会承担与私人灵魂的无限漫游之间,构成了一种独特的“灵魂辩证法”。这使他区别于纯粹书斋里的诗人,也让他的文本拥有了穿过岁月、直抵人心的多维棱镜效应。
长期的司法与行政生涯,赋予金立安一种嵌入本能的理性结构。这种理性并未窒息诗情,反而转化为他观察世界、提炼诗意的一副特殊透镜。它使得他的诗歌避免沉溺于空泛的抒情,总带着一种清晰的“看见”能力和冷静的“界定”企图。
在《裸奔》一诗中,这种特质尤为显著。诗题本身极具冲击力,但诗人的处理却非情绪化的批判或猎奇式的描绘。“只有皇帝的裸奔/才配有新装的故事”,开篇便以犀利的反讽,将个体行为置于社会寓言与权力话语的谱系中考察。“城管可以管/警察也能抓”,近乎白描地陈述规则,冷静得如同法律条文。然而,诗的锋刃转向深处:“裸奔背后的故事/未见有人关心”。法官的视角使他首先“看见”现象与规则,而诗人的心灵则迫使他去“追问”现象背后的因果与孤独。这里的“裸奔”,已超越具体行为,成为任何偏离常规、试图以“真我”直面世界却只收获误解与制裁的生命状态的隐喻。理性确保了批判的精准,而诗性赋予了批判的悲悯与广度。
这种理性提纯的意象,在其近作中愈发圆熟。《纸牌》中,外婆“不识字也赢得冷暖人心”,那副窄长的纸牌,是命运、智慧与人情的凝结物,最后“放进了装她骨灰的匣子里”。一个具体物象,在诗人克制的叙述中,被升华为承载一生的哲学符号,其情感重量因表述的节制而愈发沉郁。《九荷塘冬韵》里,枯荷的“黑瘦的筋骨戳破天空/隐喻着雄浑的汉风唐韵”,观察是客观的,但联想却磅礴纵横,在衰败的物理形态与璀璨的文化精神之间建立了惊心动魄的联结。这无疑是阅历之眼与诗心共同运作的成果。
如果说理性是金立安诗歌的骨架,那么丰沛的感性则是其血肉与脉搏。诗集最动人的篇章,往往是他卸下公共身份,回归儿子、孙辈、故乡游子乃至纯粹生命思索者角色时的深情书写。这些作品构成了其诗歌情感的深井。
《八月廿六日祭》是一首泣血之作。“心知道,这一走/走得狠,不回头”,口语般的重复,是巨大悲痛面前语言的失重与执拗。“白天,眼泪往心里流/夜里,眼泪把枕浸透”,这对称的朴素陈述,其感染力胜过万千修辞。法官的严谨让哀思有清晰的脉络(时间、事件),而诗人的赤子之心让每一道脉络都奔涌着滚烫的情感。在这里,公共身份的“刚”彻底让位于私人情感的“柔”,展现了其灵魂维度的完整。
同样,《祖屋》是对精神原乡的深沉凝视。“斑驳潦倒的姿势/恰似我年少的时光”,物我互喻,精准而苍凉。离乡奋斗的历程被喻为“用初出茅庐的镰刀/砍出生存的一块土壤”,坚韧中带着历史的粗粝感。当“回到祖屋没有了幻想/像犯错的孩子蹲在一角”,那种历经世事后在生命起点前的忏悔与安宁,复杂难言。这种对根脉的追寻与反思,超越了简单的乡愁,触及现代人普遍的精神漂泊与身份认同。
即便在《飘雨的日子》《我和月光》这类早年的青春抒怀之作中,那种“潮湿的心情”、“泠泠的忧伤”也因其真挚而未随时光褪色,成为了解其情感底色与诗艺起点的珍贵标本。从青春感伤的清溪,到中年沉郁的深河,其感性洪流的河道日益开阔深邃。
金立安诗歌最高的艺术价值,并非理性与感性的简单并存,而在于二者经由其独特生命经验的熔铸后,所产生的化学反应与哲学升华。他的诗常于具体处起笔,却总能驶向抽象的思辨彼岸,实现从“法官诗人”到“诗人哲人”的飞跃。
《星火与街灯》便是一场充满戏剧张力的微型哲学辩论。街灯与星火的争执,是关于“近处的实用”与“高远的理想”、“暂时的遮挡”与“永恒的光明”的隐喻。诗人没有给出非此即彼的判决,而是呈现了二者的局限与价值:街灯照亮行人的路,星火最终让“大地都白亮亮”。这体现了经过人生历练的辩证智慧——理解不同维度的价值,并相信时间会给予公正的答案。
《灵魂搀扶》则是一次深入精神困境与救赎的探险。“没有窗户的宇宙”、“行尸走肉般游荡”,描绘了现代性的灵魂黑洞。然而,救赎来自“灵魂搀扶着五线谱/在演绎海的节奏山的铿锵”。将抽象的灵魂互助,具象化为共谱雄浑乐章,这个意象的诞生,无疑是理性(对困境的结构性认知)与感性(对救赎的坚定信念)完美结合的产物。它指出,超越个体的孤绝,在于与另一个灵魂建立共振的、创造性的精神联结。
在最新的《燕子矶抒情》中,这种辩证与升华抵达了历史与文化的层面。面对“凝结成一堆俏丽的石头”的燕子矶,诗人“搬来蜡黄的典籍”翻找,却发现“在时间的流里未见记录”。历史的浩瀚与个体的渺小,文明的遗迹与意义的虚空,构成巨大的张力。最终,“那无法破译的生命密码/早已耗尽我拖拖拉拉的青春”,这声叹息,是个体的,也是普世的;是感性的遗憾,更是理性的认知,承认在永恒面前,探索本身即是意义。这种慨叹,因其坦诚与清醒而显得无比庄严。
诗集《飘雨的日子》是一部“入世”之诗与“出世”之思的交响。金立安先生以他跨界的人生,实践了一种珍贵的诗歌伦理:不回避身份的重量,不割裂经验的整体,将生活的所有赠予,包括它的重负与荣光、它的规则与激情,都转化为诗的养分。他的诗歌,是理性与感性的和声,是职责与初心的对白,是社会表象与生命本质的互证。在这部诗集里,我们读到的不仅是一个法官的哲思、一个官员的情怀、一个诗人的敏感,更是一个完整的、在时代中砥砺前行又不断向内探索的鲜活生命,如何以其全部的复杂性,诚恳地写下属于自己,也共鸣于众人的诗行。这或许就是“跨界书写”所能抵达的最深刻的艺术价值,它让我们看到,灵魂的丰富性,永远大于任何一种身份的界定。
(作者邹雷系文学创作一级,作家,江苏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)

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