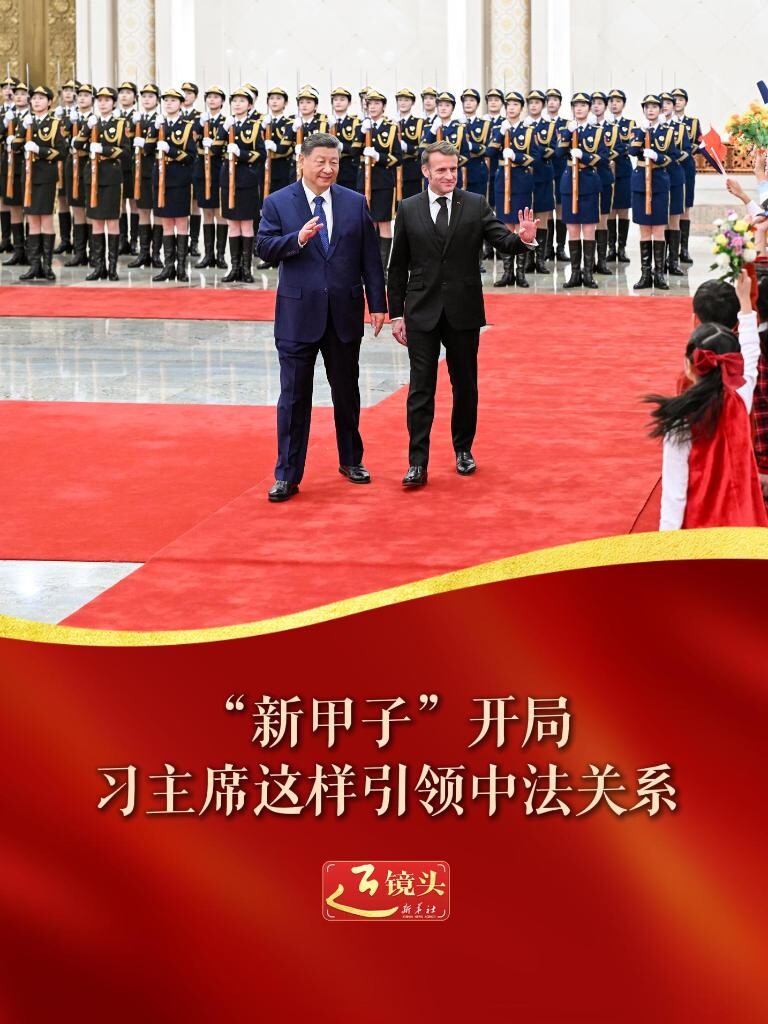当看到“终止Ⅲ级响应”的新闻时,被下派到街道的佛山当地机关工作人员刘睿感叹,“终于告一段落了!”
8月26日下午,广东佛山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称,佛山市政府决定终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,疫情防控策略将由应急处置转为常态化防控,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。
在这场对抗基孔肯雅热主要传播者——白纹伊蚊的战斗中,人类取得了阶段性胜利。
然而一些居民在防控过程中察觉,蚊子比以前少了,却也更难消灭了。8月中旬,有专家指出,广东的蚊子对菊酯类杀虫剂已产生抗药性。
抗药性意味着什么?人类该如何应对?暂时的胜利让人们回归日常,也带来新的思考:或许,人与自然之间并非谁控制谁,而是需要在不断调整中找到动态平衡点。
蚊子更难杀了
8月24日,台风“剑鱼”来了。“台风前后,蚊子会多一些。”回到家的中山居民夏琪看到纱门上停了三四只蚊子,这是她近一个月来见到蚊子最多的一次。
25日中午,消杀人员金勇刚结束佛山一所中学的消杀任务。一周后就要开学了,他所在的消杀公司收到不少学校的订单。这段时间,公司业务量大增,许多企业、机构找他们消杀。
佛山某城中村,菜市场里摊贩叫卖,老人聚着聊天纳凉。一位餐饮店主称,村里现在没什么蚊子。
23日下午,一位研究者在珠海高新区一栋办公楼捕蚊。吸蚊器和蚊笼是他行李箱中的常备工具。一小时后,蚊笼中捉到十多只蚊子。对方解释,作为专业人士,在蚊子多的地方,一小时能抓上百只。这次捉到的几只,多来自下水道附近的“卫生黑点”。蚊笼中的蚊子数量间接反映出防控成效。
7月初基孔肯雅热疫情暴发后,佛山当地街道将居住区划分为多个网格,每个网格由居委会、派出所、卫生站人员组成团队,负责张贴提示、登记住户信息、排查发热及积水情况、派发灭蚊片、清理杂草杂物等。发现发热或积水,须及时通知户主并跟进。清理消杀中还动用了无人机,准确定位杂物堆积和积水黑点,立即处理。
与之相关的布雷图指数,此时已降至5以下。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郑爱华解释,该指数通过检查积水容器及伊蚊幼虫孳生情况计算得出,是评估登革热、基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的重要指标。布雷图指数在5以下,属于相对安全范围;介于5到10之间,提示该地区存在低度风险;介于10到20之间,提示该地区存在登革热流行中度风险;高于20,提示该地区属高风险地区,有暴发风险。
不过,也有人感到蚊子似乎更难杀了。
佛山某区级机关单位的杨珊在近期一次消杀后注意到一个细节:不远处,两三只蚊子仍在盘旋。她还发现,蚊子似乎总在消杀后不久再次出现。另一名工作人员则表示,如今被蚊子叮咬后,包肿得更大,且四五天不消,挠破后容易留印,蚊子不但难杀,好像也更毒了。
很难说这些细节指向蚊子的抗药性提升。不过,“如果你在点着蚊香的半夜,还起来打蚊子,那你就感受到蚊子的抗药性了。”郑爱华说。
杨珊看到佛山三水区相关单位近期得出的监测结果:白纹伊蚊幼虫对残杀威的抗药性指数为4.53(低抗),对双硫磷为16.86(中抗),对氯菊酯为41.43(高抗)。白纹伊蚊成蚊对马拉硫磷的死亡率为81.67%,属“可能抗性种群”;对溴氰菊酯的死亡率为25%,属“抗性种群”;对恶虫威的死亡率为98.33%,仍属“敏感种群”。
日前,顺德区也测定了白纹伊蚊成蚊对4种杀虫剂的抗药性,结果与三水区基本一致。
蚊子抗药性变强
蚊子出现抗药性是一个老问题。
郑爱华说,早在2.26亿年前的三叠纪就出现了最早的蚊子。当时人类的祖先仍是水陆两栖动物。能历经数亿年演化而不被淘汰,蚊子自有其生存之道,人类难以彻底消灭。
19世纪,人类合成化学杀虫剂并广泛应用于农业和公共卫生领域,如农业害虫一样,蚊虫抗药性问题也逐渐显现。
简单来说,抗药性就是连续使用某类杀虫药剂后,蚊子发展出对这类杀虫剂一定剂量的耐受能力,这种能力可遗传到下一代。只要持续使用杀虫剂、驱避剂,蚊子就必然产生抗药性。
令郑爱华担忧的是,短时间内,大规模、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的升级,打破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平衡。
一个周末,小雨淅沥,中山水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王颖被派往某村协助工作。“当地布雷图指数达到20了。”村干部告诉她。
指数“爆表”的是一片工厂区。王颖被派往的厂区面积近3000平方米,积水点多集中在电动车棚周围——因水泥地面浇筑不平,墙角低洼处容易积水。她看到不少积水混杂泥土、垃圾、青苔,明显属于卫生“黑点”。厂区周围还有多处水洼。村干部称这些都是隐患,要求他们立即清理。
王颖说,大多数工作人员并不太了解生态平衡和抗药性方面的知识。她注意到药剂包装上明确标识每平方米3克的用量标准,但实际操作中,几乎没人带秤,往往直接倾倒。
村里一位连续多年参与防蚊的工作人员告诉她,这类药“没有这么严格的讲究”。在蚊虫孳生地附近多倒才有效。对方边说边抖抖包装袋,将药物倒入窨井。“如果杀不死,那就多倒点。”至于抗药性,他们相信大点剂量总能见效。
以往下雨前,蜻蜓——蚊子的天敌低空盘旋。最近几个月,王颖感到,蜻蜓比往年少了。她住的小区外有条水沟,夏夜总能听到蛙鸣。如今,蛙鸣消失了。
因消杀人力紧张,刘睿被要求每个工作日有半天下沉社区防疫。十个工作人员一组,每组在一个社区轮值两周,再转往下一处。消杀防控后,他发现周边蚊子少了,病例增速也放缓了,“即便穿短裤上街,也不太被叮了”。但他注意到,路边的灌木丛被铲平。他感到难过,消杀一种昆虫可能导致其他物种死亡。刘睿说,“我们不能放任不管,但也不能过度干预。”若其中一环遭到破坏,势必影响整个生态链。
郑爱华担忧的是,短时间内,大规模、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变化,蚊子因此更难杀死。“对长期防控而言,今年的用药终点就是明年的起点。”人类不得不持续增加剂量和频次,投入更多成本——这不是可持续的防控方式。
他进一步解释,事实上,蚊子传染病毒有“窗口期”,正式名称是“外潜伏期”。蚊子叮咬感染者后,病毒需在蚊子体内“潜伏”1周多,才能通过再次叮咬人传播病毒,而成蚊的寿命仅1至2个月,其所携带的基孔肯雅热病毒不会传给下一代。此外,蚊媒病传染传播有几个决定因素,包括:蚊子密度、人口密度、人蚊接触强度。因此,清除蚊子孳生地、消灭成蚊和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是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。
如何学会共存
佛山禅城区居民梁刚感受到生活的变化是在8月中旬,台风“杨柳”影响佛山之时。当时,暴雨导致佛山部分区域内涝,他所在的小区有车辆被淹,他的车因停在高处而幸免。
台风过后,梁刚发现内涝与防蚊措施有关:街道在下水道铺装纱网,却被落叶垃圾堵塞,导致排水效率骤减。他把人们生活的城市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系统。“装纱网是必要的,但任何措施都可能带来新问题,我们应该提前研判、系统解决,而不是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。”
城市治理如此,面对自然亦如此。
郑爱华表示,大家无需对蚊子的抗药性过于担忧。具有抗药性的蚊子,其环境适应能力相对于敏感的蚊子往往更差。在不用杀虫剂的时候,蚊子的抗药性种群会发生可逆的变化,但前提是环境中还有敏感的蚊子种群。但如果蚊子全部产生了抗药性,那这种可逆性变化就很难发生了。
此外,为了延缓抗药性产生,在消杀用药时可以采用“鸡尾酒”方式,即消杀过程中,混合两种不同靶点或者不同杀伤方式的药物,延缓抗药性的形成;也可使用“生物控制”方式,如通过释放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,使其与野生蚊交配后不育后代,从而降低总体蚊子密度;还可研发新型的蚊虫驱避剂、杀虫剂等,有效规避蚊子对现有杀虫剂的抗药性问题。
这个夏天,佛山在全市范围内多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,全面清除蚊媒孳生地,筑牢基孔肯雅热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。但蚊媒疫情也对爱国卫生运动提出新课题。我国以前应对的虫媒传染病,如疟疾、血吸虫病和乙型脑炎等主要发生在农村。而现在流行的基孔肯雅热的发病规律显示,人口密度是关键指标。随着城市化推进,城市人口密度增加,该病更像一种“城市病”。针对佛山这类有高密度城中村的地区来说,它介乎城市和农村之间,其路面、管网系统有所欠缺,产生的卫生死角也与以往不同。郑爱华呼吁,需在过去有效方法的基础上,优化出一套适应未来复杂城市环境的防控策略。
人与环境、政策与执行、集体与个人——每一种关系,都在重新寻找平衡。
“我住在一楼,有些潮,蚊子也多。”早在多年前,住在中山一小区一楼的夏琪给家里装了纱窗、纱门。她还学会通过观察纱门、纱窗上停落的蚊子数量,判断是否点蚊香或涂抹“蚊怕水”。
夏琪觉得,防蚊已成为生活常态。常态化防控加上每个人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,才是有效措施。
每天回家时,她都先拍打纱门惊走蚊子,再开门侧身进屋。白天在室外点蚊香,夜晚室内用温和的蚊香液,床上加装吊顶蚊帐……她逐渐学会与蚊子共存。
王颖参与到村里宣传基孔肯雅热的工作。她发现,某些村民家中积水多是有原因的。这些村民家的农田在地势较高处,缺少水系灌溉,但当地早就禁止打井,而用自来水灌溉不仅成本高,村民还担心氯气影响作物生长。于是,村民用水缸、桶收集雨水。作为一名水务工作人员,王颖觉得应看到居民需求,尽力为他们解决困难。
就读社工专业的彭雅在佛山某街道实习。“大家并不焦虑,只是每日做好该做的防护。期待生活回归正轨。”彭雅说。
8月26日,“终止Ⅲ级响应”的消息传出。彭雅感叹道,这一切离不开政府各部门和市民的共同努力。杨珊期盼能有个正常双休,好好休息一下。
佛山乐从镇南区公园内设了五个消杀网格,每个网格间隔六七十米。一个喇叭播报着公园每天上午7点至9点、下午5点至7点开展灭蚊消杀。当天下午5点,公园里有老人举着麦克风唱起了歌;还有年轻夫妻带着孩子在公园玩耍;一对老人来公园散步,志愿者拎着驱蚊水,喷在老人的手臂、脚踝处。
给桥底的草喷完药后,一名消杀人员拎起管子走向下一个消杀网格。(除郑爱华外,其他人物均为化名)
解放日报记者 郑子愚 实习生 甘煜敏